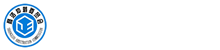1995年12月17日,香港高立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光大)作为甲方,香港东港大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明道)作为乙方,广东五井农工商综合服务部作为丙方三方签定了《广州总统大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经丙方认可,甲方同意将其在酒店持有的34.5%的股份有偿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甲方的出资转让。同时约定甲方以高速货运的名义保留总统大酒店中的部分场所为甲方的租赁经营场所。此转股协议的甲方签字者为杨光大,乙方为刘明道。
同日,杨光大、刘明道根据转股协议中有关租赁经营场所的条款,又具体签署了《租赁总统大酒店潮粤海鲜楼合同》,对租赁场所进行了明确约定,并约定租赁合同争议提交在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总会)仲裁。同日还有一份《总统大酒店、潮粤海鲜楼经营管理协议》,甲方由刘明道代表广州总统大酒店签署,乙方由杨光大代表潮粤海鲜楼签署。
1996年10月16日,杨光大代表高速货运(杨光大在香港注册的全资公司)与刘明道签署了一份《总统大酒店与潮粤海鲜楼补充管理协议》。该补充第4条、第6条明确规定:双方遇到合同上的争议时任何一方均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深圳分会(以下简称深圳分会)进行仲裁。此前双方所签合同有与本合同不一致的地方,以本协议为准。
后双方在履行租赁合同、经营管理协议和补充协议时,针对租赁场所外围墙体部分的使用权问题、相邻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议,经协商未果。1997年11月12日,杨光大代表高速货运,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将案件提交深圳分会仲裁。其后不久,1988年11月19日北京总会依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也受理了此案,申请人为广州总统大酒店。
[仲裁裁决要旨]
深圳分会仲裁庭认为:以上签定的《租赁合同》、《经营管理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同是本案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并且三份协议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且三份协议共同指向的客体是“潮粤海鲜楼”。2000年3月31日深圳分会作出了有利于高速货运的终局裁决,主要内容为继续履行合同,由广州总统大酒店有限公司提供依据《租赁合同》、《经营管理协议》和《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此前未提供的经营条件和场所,减付租金。
北京总会在裁决该案件过程中,被申请人杨光大提出了仲裁管辖权异议和将其作为被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异议。1999年8月17日,北京总会作出(99)贸仲字第4838号“关于X98375号房屋租赁合同争议仲裁案仲裁管辖权及被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决定”,指出:⒈租赁合同中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对本案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北京总会对以总统大酒店为申请人、以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和杨光大为被申请人的X98375号仲裁案具有仲裁管辖权;⒉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和杨光大作为本案的被申请人不存在主体资格不合适的问题。⒊本案仲裁程序继续进行。2000年1月6日北京总会作出(2000)贸仲字第0084号中间裁定书,指出:⒈本案的被申请人为杨光大先生;⒉被申请人应于2000年1月31日前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申请人的租金人民币3684702元;⒊北京总会被申请人应于本中间裁定规定的期限内向被申请人支付上述租金,逾期不支付,本案租赁合同即应终止。杨光大不服,于2000年1月23日向北京第二中级法院申请撤销中间裁决。北京第二中级法院(2000)二中经仲字第35号裁定书驳回了杨光大的申请。2000年5月12日北京总会作出了有利于广州总统大酒店的终局裁决,主要内容为终止租赁合同,并由杨光大本人支付高速货运欠付的租金。
争议双方已分别就两个终局裁决向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面对内容各异的裁决,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执行法院陷入了两难境地。
[评析]
本案系仲裁机构就同一法律关系争议作出的两个矛盾裁决而引发的一起仲裁裁决执行案件。它不仅涉及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还引起人们对与仲裁裁决有关的仲裁协议、仲裁机构的仲裁权、仲裁程序以及仲裁裁决的效力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一、本案法律关系的同一性
本案涉及三个合同,即1995年的《租赁总统大酒店潮粤海鲜楼合同》(简称《租赁合同》)、《租赁总统大酒店、潮粤海鲜楼经营管理协议》(简称《管理协议》)和1996年的《租赁总统大酒店与潮粤海鲜楼补充管理协议》(简称《补充管理协议》)。其中《租赁合同》为基础合同,规定了总统大酒店同“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双方的租赁法律关系;《管理协议》与《租赁合同》同日签定,由总统大酒店同杨光大代表的潮粤海鲜楼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出租人与承租人对《租赁合同》的补充和权利义务关系的细化;《补充管理协议》是总统大酒店同杨光大代表的“高速货运”签定的,明确将租赁合同的承租人由“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变更为高速货运,并对《管理协议》内容进行局部的补充。由于三个合同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内容合法,因此,本案三个合同都是有效的。
总的来看,《管理协议》和《补充管理协议》都是在保持原租赁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对原《租赁合同》的内容作某些修改和补充,并未丧失与原租赁法律关系的同一性。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变更的实质是以变更后的合同代替了原合同。在合同发生变更以后,当事人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的内容作出履行,任何一方违反变更后的合同内容都将构成违约。本案的三个合同共同指向租赁标的物“潮粤海鲜楼”,其内容又均与租赁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有关。故这三个合同应当视为一体,它们的订立均围绕着租赁合同关系而发生和展开,共同规范着当事人双方的租赁关系,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
在这个租赁法律关系中,出租人为总统大酒店,而承租人却先后出现了几个不同的称谓: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潮粤海鲜楼、高速货运。依据仲裁庭的认定和北京第二中级法院(2000)二中经仲字第35号裁定,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直至1998年才成立,在《租赁合同》签定时并不存在;潮粤海鲜楼是双方租赁经营场所的名称;高速货运是杨光大在香港注册的无限公司。这里需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租赁合同》是否因一方主体在订立合同时尚未成立而导致无效?二是该案是否因承租人称谓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租赁法律关系?
首先,《租赁合同》的效力并不因一方主体在订立合同时尚未成立而受影响。从本案情况看,总统大酒店从未就相对方的租赁法律关系主体资格提出异议,也从未因此而主张租赁合同无效。事实上,高速货运申请深圳分会仲裁时只是请求总统大酒店排除对租赁物的妨碍,履行租赁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总统大酒店向北京总会申请仲裁时也不过主张相对方支付租金,并请求终止租赁合同。可见,任何一方当事人都认为租赁合同有效,并且深圳和北京两个仲裁庭在裁决中也都承认了合同的效力。
第二,该租赁法律关系中承租人称谓的不同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同一性。有人认为,深圳分会审理的仲裁案件是总统大酒店与高速货运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而北京总会审理的仲裁案件是总统大酒店与杨光大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纠纷主体不同,当事人的诉求不同,故认为北京和深圳仲裁的是不同的案件。
这恐怕是一种误解。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说本案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租赁合同。但是明显的漏洞是:本案租赁物只有一个,即潮粤海鲜楼,我们无法想象总统大酒店何以能够将一物同时出租给两个主体。另外,如果是两个不同的租赁合同,那么总统大酒店在租赁期间,应该有权就同一租赁物分别向两个承租人收取租金。但事实是,总统大酒店只能向以杨光大为代表人的“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或“潮粤海鲜楼”或“高速货运”或杨光大本人收取租金。在收取租金时,总统大酒店一直是将他们等同看待的,在“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潮粤海鲜楼”、“高速货运”、杨光大之间划上等号的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大酒店,即北京总会仲裁的申请人。
我认为仲裁庭应当根据本案情况对承租人的称谓进行合理的解释。只要我们承认本案的三个合同都是有效的这个前提,就不能局限于合同中所使用的某些称谓,而应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也就是说要探究双方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本案承租人的称谓可作两种解释:一种是按照总统大酒店的做法,认为承租人为“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潮粤海鲜楼=高速货运=杨光大”,北京总会的裁决有此倾向;另一种是尊重当事人1996年达成的《补充管理协议》的规定,认为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应当变更为高速货运,以高速货运为本案租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深圳分会的裁决即如此。
我认为,第二种解释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理由是:本案承租人虽有多个称谓,但其代表人均为杨光大。以杨光大为代表人的高速货运依据1996年的《补充管理协议》已经取代了原《租赁合同》中作为承租人的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并且,在与《租赁合同》同日签定的《广州总统大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曾明确约定香港高立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光大)以高速货运的名义租赁总统大酒店的部分经营场所,这才有了《租赁合同》中租赁经营潮粤海鲜楼的具体约定。如果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考察整个案情,就不难看出本案法律关系的同一性。
二、关于两份仲裁协议的效力
上述三个合同中,只有《租赁合同》和《补充管理协议》中对因该租赁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约定了仲裁条款,其中《租赁合同》约定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总会仲裁,《补充管理协议》则约定由深圳分会仲裁。
依仲裁协议独立性规则,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因此,这两份仲裁协议的效力分别独立于《租赁合同》和《补充管理协议》,不因该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后来发生的补充、变更或者无效而 失去效力。
事实上,北京总会和深圳分会就是分别依据《租赁合同》、《补充管理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定而作出裁决的。
但是,能否以仲裁条款独立性为由而认为本案的两份仲裁协议都具有法律效力呢?
回答曰:“否!”
所谓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是指仲裁条款独立于含有该条款的主合同,它随着主合同的订立而订立,并随着主合同的完全履行而终止,但它的效力不仅不因主合同发生争议或被确定无效而失去效力,反而正因此而得以实施,发挥它作为救济手段的作用。可见,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所解决的只是仲裁条款与主合同之间相分离的关系。
但是本案的问题不在于仲裁条款与主合同之间关系的独立性,而在于先后达成的两份仲裁协议之间的关系,即两份仲裁协议是同时有效还是只有其中一项有效。结合本案情况,应当说,本案不仅存在着租赁合同的变更问题,而且还存在着仲裁协议的变更问题。当事人双方1996年的《补充管理协议》第4条、第6条明确规定:“双方遇到合同上的争议时任何一方均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依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此前双方所签合同有与本合同不一致的地方,以本协议为准。”鉴于《补充管理协议》与《租赁合同》的一体性,上述规定明白无误地表明了1996年《补充管理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已经代替了1995年《租赁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因此,在解决该租赁法律关系的争议时,真正有效的仲裁协议是1996年《补充管理协议》中的新仲裁条款。
也许有人对当事人双方能否以新的仲裁协议取代原来的仲裁协议持有怀疑态度,其实这一疑虑是不必要的。仲裁条款毕竟是当事人双方就争议解决方式所达成的一种协议,当事人可以在《租赁合同》中协议由北京总会仲裁,也当然允许他们以新的约定改变原来的仲裁条款。只要当事人双方自愿,他们有权利在纠纷发生前或纠纷发生后达成一项新的仲裁协议,以取代原来的仲裁协议。这一点,已经包含在仲裁法第4条规定的仲裁自愿原则的意义之中了。
如果放宽视野,试想一想,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允许当事人以管辖协议改变法定管辖(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除外),使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丧失管辖权,而使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取得管辖权,那么在更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仲裁制度中,当事人双方一致变更原来订立的仲裁协议,而代之以新的仲裁协议,这一权利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有人还提出了仲裁协议的可分性问题。在一个法律关系争议中,可能会因法律关系复杂而出现各个方面的纠纷,如果当事人就不同方面的纠纷约定不同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只要当事人仲裁协议的意思表示明确有效,自然应当允许当事人就不同纠纷提请不同的仲裁机构仲裁。但是本案并不属于这种情形。本案虽有两个合同涉及仲裁协议,但两个仲裁协议之间并非平行并列关系,而是后一个仲裁协议取代了前一个仲裁协议。
因此,本案的两个仲裁协议中,只有第二个才是有效的,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向深圳分会提请仲裁。
三、关于本案的仲裁权问题
作为一种民间机构,仲裁机构不享有法定仲裁权,仲裁机构的仲裁权只能来自当事人双方在仲裁协议中的授权。当事人的授权是仲裁机构享有仲裁权的基础和前提。判断一个仲裁机构对某一案件有无仲裁权,就看其是否属于仲裁协议中所约定的仲裁机构。从本案看,北京总会接受一方当事人的仲裁申请受理该案件是错误的,北京总会对本案无仲裁权。理由是:
⑴北京总会依据1995年《租赁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受理该案件,漠视了三个合同的一体性,将同属租赁法律关系的三个合同人为地分割开来。仲裁庭在本案的事实认定上有意或无意地将租赁合同关系后来发生变更的事实排除在本案审理之外,造成了北京总会依据《租赁合同》中仲裁条款的规定而享有仲裁权的假象。但是,在本案中,无论是通过曲解仲裁条款的独立性,还是将指向同一法律关系的三个协议认为分割,都无法掩盖北京总会对该案欠缺仲裁权的事实。
⑵根据上述分析,本案真正有效的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是深圳分会,只有深圳分会对本案才有仲裁权。
⑶北京总会与深圳分会同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事实也不能表明北京总会对该案有仲裁权。尽管北京总会与深圳分会同属一个仲裁委员会,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有一总会、两分会的现实决定了二者仲裁地点上的巨大差异。而仲裁地点属于仲裁协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当事人双方在仲裁协议里约定了仲裁地点,那么这一约定对仲裁机构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双方约定地点的仲裁机构对案件才享有仲裁权。在本案中,只有深圳分会才属于有效仲裁协议中约定地点的仲裁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在北京总会仲裁时,被申请人在答辩中对北京总会的仲裁权提出了质疑,指出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已变更了仲裁地点,北京总会无权仲裁此案件。但仲裁机构没有采纳该异议。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即仲裁机构能否对当事人提出的仲裁权异议,作出终局决定?仲裁机构的决定是否需要说明理由?是否可以借鉴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当事人对法院管辖权异议的决定提起上诉的规定?仲裁法第19条规定“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似乎肯定了仲裁机构有终局决定仲裁权异议的权力。但是这个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在本案中,由于当事人无法对北京总会的决定加以攻击,从而使北京总会顺顺当当地仲裁了此案。这是发人深思的。尤其是当仲裁机构成为一个自收自支的民间机构后,仲裁机构的利益驱动有可能促使其作出非理性的行为,争夺仲裁权。可以考虑引入司法监督机制,设置一种救济程序,允许当事人不服仲裁机构所作的关于仲裁权异议的决定时,可以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由法院作出最终的决定。
四、本案仲裁裁决的效力
我国仲裁法实行一裁终局制度。仲裁机构对于双方当事人提请仲裁的案件作出的裁决具有终局的法律效力,任何一方都不得要求该仲裁机构或其他仲裁机构再次裁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也不得向其他机关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一般情况下,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不仅对仲裁机构本身产生拘束力,对于双方当事人也有约束力。
但是,我国仲裁法还确立了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有权依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依法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时,该仲裁裁决即丧失了相应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就该纠纷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那么,如何识别一项仲裁裁决有效抑或无效呢?民事诉讼法217条、260条和仲裁法58条、63条明确规定了仲裁裁决有效性的判断标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项:
⒈当事人订立了有效的仲裁协议;
⒉仲裁机构对于裁决的事项具有仲裁权; ⒊仲裁程序合法或与仲裁规则相符; ⒋被申请人得到了公正的仲裁程序保障;
⒌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充分、没有隐匿或伪造情形;
⒍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没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⒎仲裁裁决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凡是一项仲裁裁决不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就可能被法院依申请或依法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由此使该裁决失去法律效力。
判断本案中的两份仲裁裁决有效与否,同样不能离开上述法定标准。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本案的两份仲裁裁决中,北京总会作出的裁决不是建立在当事人双方订立的有效仲裁协议基础之上,并且北京总会对于裁决的事项也欠缺仲裁权。基于这两点理由,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北京总会对于本案所作出的仲裁裁决是无效的,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五、本案应当如何执行
本案执行的关键是,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与北京总会作出的两个不同裁决中,广州中级法院应当以何者作为有效的执行根据。
我国法律规定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可以作为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217条、仲裁法62条),但这是以仲裁裁决合法有效为前提的。对于无效仲裁裁决,人民法院有权依当事人的申请裁定撤销(仲裁法58条)或者裁定不予执行(民事诉讼法217条、仲裁法63条)。
尽管本案出现了两个矛盾的仲裁裁决,但由于北京总会作出的仲裁裁决是无效的,自然不能作为广州中级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能够成为本案执行根据的仅限于深圳分会作出的裁决。
本案执行的具体操作步骤是:广州中级法院首先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撤销北京总会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裁定不予执行北京总会作出的仲裁裁决;然后以深圳分会作出的裁决为执行根据,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综上所述,深圳分会作为当事人双方有效仲裁协议中被授予仲裁权的仲裁机构,其作出的裁决是生效裁决,广州中级法院可以此为执行根据,依申请进行强制执行。对于北京总会所作的仲裁裁决,广州中级法院可以根据一方当事人申请裁定撤销或依法裁定不予执行。
六、北京总会在本案中的尴尬处境
尴尬之处在于:北京总会(99)贸仲字第4838号决定与其(2000)贸仲字第0084号中间裁定书自相矛盾。
北京总会(99)贸仲字第4838号“关于X98375号房屋租赁合同争议仲裁案仲裁管辖权及被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决定”指出:⒈租赁合同中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对本案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北京总会对以总统大酒店为申请人、以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和杨光大为被申请人的X98375号仲裁案具有仲裁管辖权;⒉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和杨光大作为本案的被申请人不存在主体资格不合适的问题。
但是,北京总会(2000)贸仲字第0084号中间裁定书却赫然指出:⒈本案的被申请人为杨光大先生。⒉……。
可见,北京总会先后作出的两个裁决在被申请人资格的认定上是自相矛盾的。北京总会为什么要用后一个裁决推翻自己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第一个决定中,申请人将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和杨光大都列为被申请人,目的无非是表明其请求北京总会仲裁的纠纷不同于深圳分会已经受理了一年多(请注意:深圳分会与北京总会受理案件的时间分别为1997年1月12日、1998年11月19日)并正在仲裁的纠纷。从北京总会的角度讲,将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列为被申请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仲裁机构受理案件必须以当事人双方事先订立仲裁协议为前提,而本案中总统大酒店只是与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订立了仲裁协议,而从未与杨光大个人订立仲裁协议。如果直接把杨光大列为被申请人,北京总会在杨光大提出仲裁权异议时,就无法说明自己仲裁这个案件的依据何在。北京总会出于争取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的考虑,当然在杨光大提出仲裁管辖权异议时,认定被申请人之一为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在这里,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是北京总会介入此案的桥梁。
但是,北京总会在取得对此案的“仲裁权”和程序控制权后,就将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一脚踢开,被申请人就变成了杨光大。直白地说,北京总会玩了个“过河拆桥”的把戏。但这是一个质变,它使北京总会陷入了两难境地:
第一,被申请人的变更使北京总会丧失了对本案“仲裁权”的基础。即使我们撇开北京总会根本就无仲裁权这一事实,单纯就北京总会变更被申请人而言,就足以使其仲裁权丧失。很明显,被申请人杨光大从来不曾以个人名义与申请人签定租赁合同,更不曾与申请人订立仲裁协议,那么北京总会凭什么仲裁此案呢?!
第二,杨光大=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
为了说明自己对本案有仲裁权,北京总会可能会提出: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形式上是香港高速货运有限公司,但实质上为杨光大。故将杨光大变更为被申请人不影响北京总会对本案的仲裁权。北京总会(2000)贸仲字第0084号中间裁定书和北京第二中级法院(2000)二中经仲字第35号裁定书中都采用这种观点。
但事实并不如此。杨光大在北京总会仲裁过程中多次提出了仲裁权异议和主体资格异议,一再声明本人与申请人之间从未签定租赁合同,签定合同的是自己所代表的公司,并且一再指明原《租赁合同》订立后双方又签定了《管理协议》和《补充管理协议》,对原《租赁合同》的内容以及仲裁地点作了变更。但是,奇怪的是,北京总会根本不顾及本案法律关系的同一性,而是人为地将原租赁法律关系加以分割。
我们更不能理解的是,北京第二中级法院(2000)二中经仲字第35号裁定书第2页在“经审理查明”的事项中涉及《补充管理协议》的内容时,为什么只列举补充协议第4条前段的规定,而对第4条后段关于“此前双方所签合同有与本合同不一致的地方,以本协议为准”的规定却不敢列举?而且在“经审理查明”中描述了本案案情从《租赁合同》到《管理协议》和《补充管理协议》的变化后,为什么不敢对《租赁合同》、《管理协议》和《补充管理协议》三个合同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或哪怕是一点提示性解释?为什么在匆忙列举案情后就对北京总会所作的变更杨光大为被申请人的裁定及其理由进行简单的附和?
对于北京总会,我也有同样的追问:为什么不尊重当事人双方后来签定的补充协议,而是人为地分割租赁法律关系,强行将被申请人变更为杨光大?为什么不正视当事人双方仲裁协议中仲裁地点变更的事实?究竟是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重要,还是仲裁机构自身的权力或利益重要?……本案可以提出许多为什么,我期待能得到有关方面理性的回应。